需要指出的是,在发电领域,由于单位装机容量造价仍然较高,同样1亿美元的总投规模,可形成的新增清洁电力装机容量要少于传统化石燃料装机容量。这给很多需要快速增加发电能力、解决经济发展供电瓶颈的不发达国家造成很大的压力,在资金短缺和短期发展目标压倒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情况下,燃煤电站等传统化石燃料电站仍然是不得不做的现实选择。
虽然缺乏精确的统计,金融业内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价格相比传统能源项目要高。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当然是风险高低不同,其次就是传统能源领域的借款人议价能力普遍较强,而清洁能源行业的融资主体一般都是中小型公司。但从趋势看,这个领域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融资议价能力的因素会逐渐变得不太重要。
虽然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的成本在不断下降,在目前阶段,一定形式的清洁能源补贴仍不可少,甚至是获得融资的关键因素。根据近期英国风能协会(British Wind Energy Association)的测算,直到2020年,英国大规模的陆地风电场发电成本可以降低到65-75英镑/MWh,与英国的燃气联合循环机组相比具备一定程度的成本优势。这也意味着未来五年,陆地风电很难在公开市场与其他形式的能源展开竞争,补贴仍然需要。
除了广为人知的电价补贴和税收优惠,融资支持也是清洁能源补贴的一种通行模式。例如在本次圆桌会上,美国进出口银行介绍了对于清洁能源技术的出口融资支持措施,其中最具含金量的就是长期信贷支持产品。在这一产品项下,如果一家中国公司进口了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就有资格申请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长达18年、固定年利率2.79%的融资或担保支持,与资本市场上7年左右、年利率5%上下的商业信贷相比极具竞争力。
融资挑战:问题依旧
虽然清洁能源融资仍是在成熟的融资模式框架内进行,但与传统能源融资相比,仍然面临几类较为特殊的挑战:
一是管制政策框架的稳定性、专业性和有效性。能源行业是高度“管制敏感(regulatory sensitive)”的,立法和政策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重要的行业变化,对于清洁能源尤其如此。虽然从全球范围内来讲,清洁能源是管制者较为偏好的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有一个稳定、专业、有效的管制框架。
比如因为各国政治周期的变化,导致对清洁能源管制政策、财政支持力度和方式的频繁调整,打乱资本市场的预期;因为管制机构缺乏对清洁能源投融资的深入研究,导致投机者利用管制漏洞套利,偏离原有政策目标,而管制者反过来实施对所有投资者的惩罚性措施。
近年来比较经典的案例是2013年保加利亚政府宣布回溯性地向入网的可再生能源电站征收高额所得税和入网费,严重扰乱了保加利亚的清洁能源市场,打击了相关企业的营收和盈利,不仅抬高了此后保加利亚清洁能源项目的融资价格,甚至一度导致不少项目融资终止。
二是财政补贴承诺的可执行性(enforce ability)。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14年清洁能源进度报告》(Tracking Clean Energy Progress 2014),全球各国政府目前每年给可再生能源1000亿美元补贴,这还不算各项税收减免等财政性措施。问题是,这种补贴长期可持续么?如果不可持续,是否意味着从长期来看,财政的补贴承诺存在可执行性的问题?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这个经济周期里,无论大国小国,政府支出压力都在增大,财政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如危机时刻的刺激性开支、社保医保开支、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后的安全防务费用,这都属于财政刚性支出。比较而言,清洁能源补贴支出刚性较弱,降低或取消的政治代价基本可以接受,而且政府在应该履行补贴义务时,增加清洁能源装机容量的政策目标已部分实现。
这些因素都为清洁能源财政补贴能否顺利执行打下问号。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财政纪律比较严格、补贴承诺履行比较好的德国,清洁能源融资较为便利,而在某些风能、太阳能资源禀赋好得多的国家,融资却不那么容易。因此,对于清洁能源的开发商和融资银行而言,即便是签署了完善的法律文件,仍然需要关注补贴如何执行与是否到位的细节问题。
三是清洁能源传输系统/输变电能力的约束。我们现在使用的输变电网络基本还是按照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设计的,连接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大型基荷电站和电力消费中心,运行模式是在安全稳定的硬约束下实现效率优先。但是某些重要的清洁能源的生产本身较为分散(主要指风电、太阳能),可靠性也低于化石能源基荷电站,稳定并网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虽然分布式发电、智能电网、大规模储能等技术正在兴起,但从融资的角度看,如何确保某些清洁能源顺利上网并输送到终端用户,实现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
下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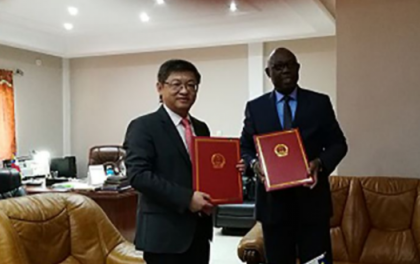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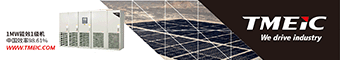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