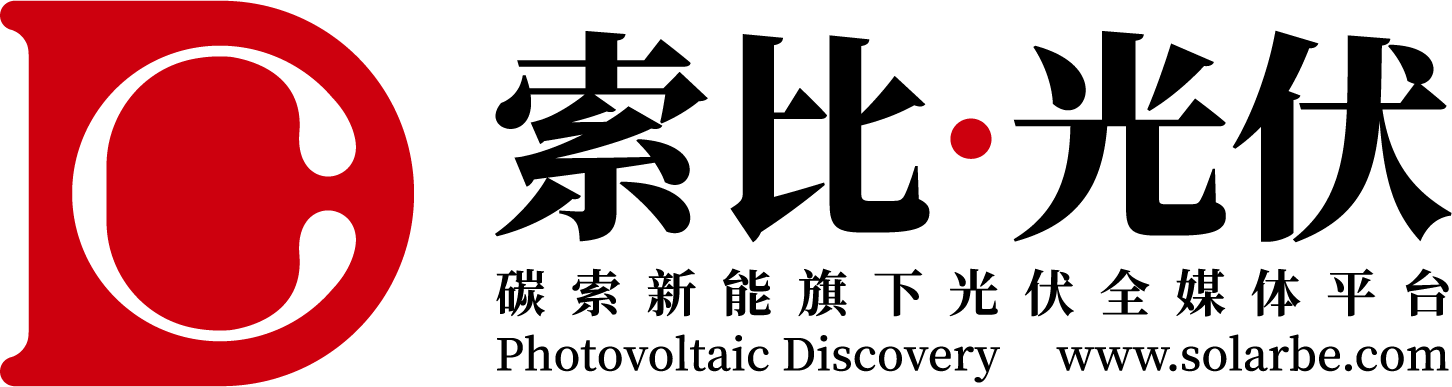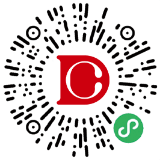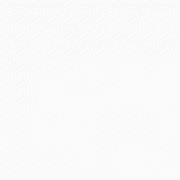过去20年的光伏产业只了干一件事情,那就是向世人证明光伏是最清洁、最有成本竞争力的能源,光伏产业做到了。2019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占全部电力新增装机规模的45%,是各类新增能源中增长最快的能源。中国光伏产业同时做到了投资规模、先进产品、电站建设、发电规模多个世界第一。
成为最有成本竞争力的能源后,光伏产业当前还有三大优势:一个是习主席不久前向世界宣布,中国争取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风光发电装机达到1200GW以上;一个是国家能源局说,“推动新一代电力系统建设,确保大规模光伏发电的接入和消纳”;再一个是研究报告说,到2050年光伏发电成本还将下降57%,同时“根据赖特定律得出结论:光伏发电能力每增加一倍,太阳能电力价格就会下降30-40%”。光伏产业的发展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其速度还将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遗憾的是,受日照影响不能平稳输出是光伏发电的天然缺陷,而必须平稳输入却是电网的基本要求,这就注定了当前光伏发电的并网上升速度无法满足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速度。一般的说法是传统电网只能接受不大于30%的不稳定电源,已经拥有强大成本竞争力的光伏发电正在快速趋近这一天花板。结果就是光伏发电成本竞争力越大,与电网接受力的矛盾越大。
更遗憾的是,光伏发电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大规模被电网主动接受的好方法。为了找到好办法,光伏产业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已知的有“光伏+电池储能”、“光伏+抽水储能”、“光伏绿氢一体化”、“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等等。但是或因成本太高、或因涉及行业太多、或因应用场景太丰富,一时难有结论。
光伏电站安装量的快速增长,电网接受力的严重受限,决定了当前光伏产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需要证明光伏发电的成本竞争力,转变为需要证明光伏发电的电网接受力。只有电网张开双臂拥抱的电源,才是最有竞争力的电源。
“证明电网接受力”比“证明光伏发电成本竞争力”要难的多。
“证明光伏发电成本竞争力”主要是光伏产业链内部的事情,相关要素少,“证明电网接受力”是跨多个行业、多种技术的事情,相关要素多。它既涉及电网、储能、多种能源等多个产业的不同利益,又涉及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的不同发展水平和相互结合。过去是技术进步决定光伏一个产业的成本竞争力,未来是技术进步决定多个产业的各种利益关系,技术链从来是最复杂的价值链;
“证明光伏发电成本竞争力”是一个加工产业的进步过程,是线性发展的,目标清晰、路径清晰,“证明电网接受力”是一个新业态的创造过程,是生态化发展的,目标清晰、路径不清晰。新业态就是综合能源服务、智慧能源服务,它是由源、网、荷、储等大量不同需求场景,调频、调峰、调压、备用、黑启动等不同辅助服务市场构成,目标是通过能源网架体系、信息支撑体系、价值创造体系来实现清洁电力供给的最优化。实现这一目标,已经不是过去几家电力企业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由不同地区、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基因的企业,甚至可能是电力企业也可能不是电力企业的企业才能解决的问题;
“证明电网接受力”的时间,比“证明光伏发电成本竞争力”的时间要紧迫的多。过去实现光伏发电平价上网,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表,是可以讨论的,例如早期光伏发电平价上网路线图,权威机构设定的实现时间是2017年,而实际的实现时间是2021年,中间几经变化。而2030年实现“碳高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一个确定的时间表,是中国向世界的严肃承诺,是不可讨论的;
“证明光伏发电成本竞争力”的过程有可学习的案例,“证明电网接受力”的过程没有可学习的案例。过去中国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每遇困难,总可以找到一个先进国家的案例比照前行,相关用词也可沿用,当前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无人区”,没有案例可参照,甚至没有统一用词,有用“智慧能源”的,也有用“数字能源”的,例如不久前华为就发布了“数字能源的十大趋势”;
“证明光伏发电成本竞争力”靠的是政策的力度,“证明电网接受力”必须靠电力市场的成熟度。2021年开始,大规模的光伏发电补贴和确保上网的政策没有了,但是确保有成本竞争力的光伏发电上网的电力交易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已经成为当前“证明电网接受力”最大、最紧迫的问题。
当需求一定的时候,“证明电网接受力”的难题越多、越难,代表着机会越多、越好,当前如何让光伏发电成为电网最受欢迎的电源,不仅是光伏产业主要矛盾的转换,更是光伏产业投资的下一个风口。2020年,A股光伏企业被资本热烈追逐,总市值增长了一倍以上,既是资本对过去光伏发电成本竞争力市场的认可,更是资本对未来电网接受力市场的预期。
参考资料:
《2019年光伏、风电占全球新增装机比例升至67% 化石燃料装机占比下滑至25%》
《国家能源局任育之:将出台建筑物上安装光伏强制性国家标准》
《风电、光伏仍有大幅下降空间!2020-2050年各类发电技术装机成本预测》
《华为重磅发布数字能源未来十大趋势》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是体制改革与机制重构》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2101/18/3340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