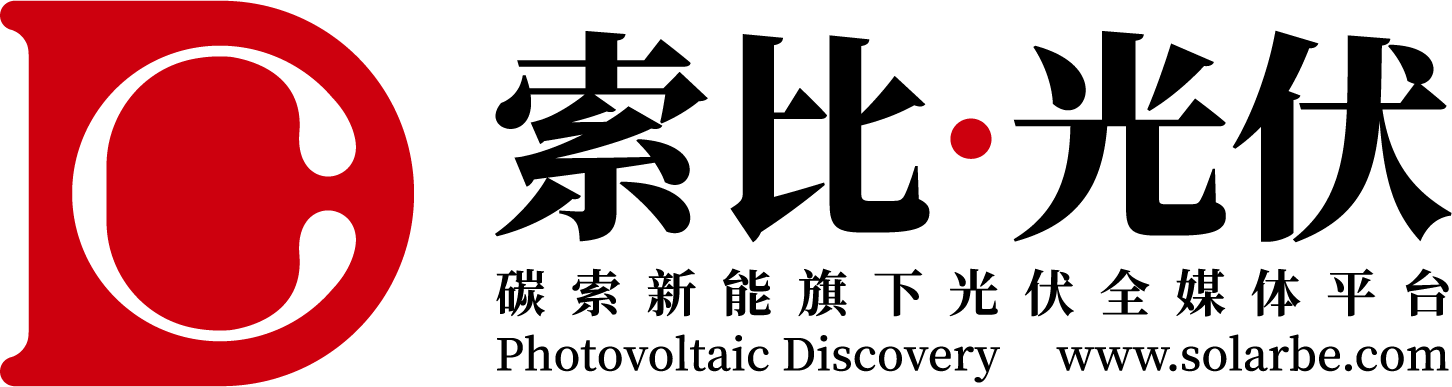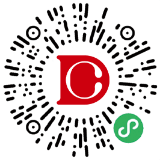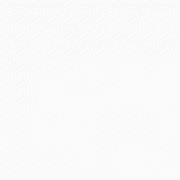2007年进入光伏行业的时候,正好赶上光伏极速发展的时期——说高速都嫌慢,说极速更确切——每家每户都供不应求,投资人和四大忙得日夜颠倒,纳斯达克和纽交所的上市钟被中国的光伏企业不停敲响,客户开着车在各个工厂门口等货,报关员每天都要统计海外出货。盛事养兵,我赶上了这个好时候,在市场部做着调研员这种不咸不淡的工作。
2007年2月份,当时从事光伏相关生产的公司,我记得很清楚,是262家,其中还包括十几家很小的做离网路灯的企业。当时ENF官网上的数据是150多家,我们的调研数据完胜。2007年5月份,我所在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了。到2007年12月31日,公司员工已经快2000人,而当年1月4日入职的我,工号是146。
人生最精彩的部分在于你也不知道你的蝴蝶效应从何而起。我的改变就因为在一次碰头会上用英语提了个问题,而销售部老大觉得正缺会英语的拓展类人才,于是把我调去业务拓展部做组件业务拓展。然后公司收购了下游两个组件厂,而我们BD部只有我一个人懂组件,于是我又顺理成章成了销售部一员。
再后来,公司内部调整,我莫名其妙成了亚太区经理。然后若干分区从我的管辖范围里被剥离,比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只要当地有政策的都被独立成一块,最后剩在我手里的市场——印度。
佛经里说要“悟空”,因为“空”才能接纳。我对印度既没偏见也无期待,踏上第一次旅途、写了第一封邮件、接待了第一个客户。一切平和,非喜非怒,直到第一个大单谈成。成功的喜悦让我对印度这个福地好感倍增。再后来某一次去印度出差,一路晕机过去一路呕吐回来,回国才发现有了喜。于是我挺着个大肚子陪着上门的印度客户验厂、看装箱、扫barcode,来来回回。
2011年之后,光伏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各个国家补贴政策开始递减,而天平这头的产能还在盲目扩大。供不应求变成供大于求,欧洲市场血拼短刀的厮杀就开始了。各个大佬纷纷在欧洲港口建仓库,打时间差做现货销售;接着欧洲先双反,第二年美国再双反。
然后是外贸下滑的同时,2011年秋冬,我在家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刷手机看光伏新闻:国内项目风生水起,无数人跑去西北和内蒙大兴土木。半年之后,路条倒卖、皮包EPC总包、电站开发、电站收购、基金介入、工厂赊销、产品入股……一时好不热闹。
2012年的冬天,我终于萌生了退出光伏的想法。
一次吃火锅,我忽然发现自己变得格格不入:他们是卖逆变器的、做接线盒的、做TPE背板的、做组件生产的,但他们都想着圈屋顶包装成项目然后申请补贴去“赚”钱,而我只担心最后这个项目发出来的电是否符合电网标准。
当我提出疑问,回应我的是一片哄笑。他们不在乎并网,反正金太阳只管安装量不管发电量。这个政策设计犹如黑洞,诱惑着人们。此时的金太阳项目已经把国内大部分B级产品消耗殆尽,而优质A类组件竟然囤积仓库无人问津。
难道不应该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吗?难道不应该首先保证研发资金吗?
不喝酒的人在醉酒者狂欢的聚会里无所适从,而醉鬼们觉得清醒的人是异类。
利用政策缺陷赚钱是商人本性无可厚非,但政策变化时,赌徒们充分暴露了人性阴暗:骗、哄、赖、拖欠。一场又一场的官司充斥着新闻,闹剧不断上演。人性的黑暗甚至在全球扩大,连东欧和印度的开发商都学会拿着PPA和路条来中国赊购组件和逆变器。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602/06/1745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