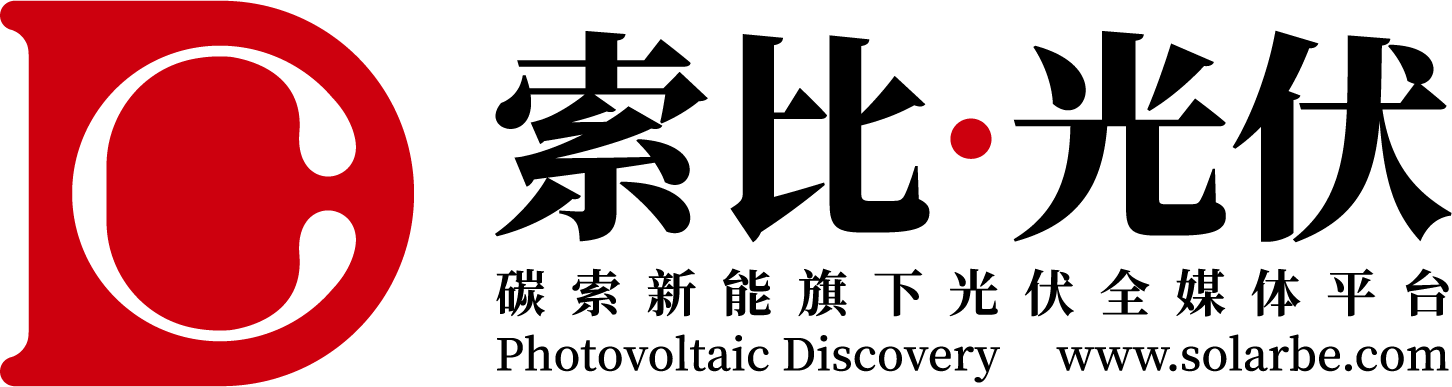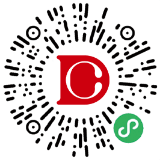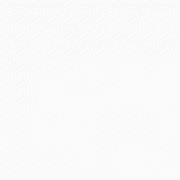黄勇告诉记者,“在政府文件和报纸杂志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熟悉的词汇——产业政策,不同于财政、货币、金融、贸易等世界各国共同的基础性经济政策,这是我们作为转型国家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主导性经济政策上的最大差异。”黄勇认为,在发展初期我国以速度和赶超为首要目标,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目标,随着经济发展从赶超阶段进入常态运行,产业政策的许多弊端也愈发显现。“产业政策往往是短期的或者有时间限度的,且政府主导,行政手段居多;而竞争手段则是长效机制,它是市场化的,按市场规律办事,两者有显著和实质性的区别。”黄勇并不讳言,“光伏产业是最典型的例子。为什么我们某个产业政策一出,企业家们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争着上项目,因为有政府补贴,有银行贷款,有各种政策性支持。如果一个企业家投身某个新兴行业,大部分的精力不是研究市场而是向政府要钱,这个行业迟早都会出问题。”
黄勇表示,“政府的主导性作用绝不应是为特定经营者群体提供特供产品,而是提供以市场竞争机制为核心的优良的市场环境这一公共产品。”让黄勇高兴的是,最近他在参加中欧竞争政策对话时发现,关注层面从具体执行转向政策设计,“今年国家发改委提出的题目讨论议题有两个,一是国家援助制度,二是普遍经济利益的经济补偿服务问题,这意味着竞争政策要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目标和依据,政府制定其他政策必须考虑是否符合竞争政策,必须考虑是否有利于形成和维护竞争机制,这就是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目前,竞争政策在整个官方的经济政策工具组合中处境边缘,政府在管理经济的过程中,仍然习惯推出被视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的产业政策,但黄勇却满怀信心,“市场的力量谁也无法阻挡,随着人们对市场认识程度的深化,竞争政策对于保障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政府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政府应当将竞争政策提升为我国基础性经济政策,才能培育出一个良好的国内竞争环境,使好企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对此,黄勇的看法是,“1979年我国就提出要建立统一市场,说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我认为思路应该有所调整。”黄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我国通过文件打破地区封锁的效果并不明显,实际上,《反垄断法》对于规制行政垄断、地区封锁有细化具体且系统的规定,可以为瓦解地区封锁提供有力武器和法治保障,中央政府应该将《反垄断法》纳入其整治地区封锁的综合措施之中,彰显其效力,助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的建设完善。
黄勇解释,行政垄断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超越了其合法权限的行为,突出表现为地方政府实施的地区封锁行为,在经济性垄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扭曲和排除了竞争,导致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社会资源得不到合理优化配置。“《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政策最重要的法律工具,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对于行政垄断的专章规定,是中国反垄断法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显著特点之一。《反垄断法》授予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调查、认定违法、公开曝光,甚至建议上级监督机关处分相关政府责任人。”黄勇反问,“为什么不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呢?立法的这一特殊安排显示了行政垄断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与重要性,通过一个个案件的具体办理可以不断推动社会的认知和进步。”
黄勇最后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竞争政策提出了新期待,深化我国市场化程度,优化非公经济企业成长环境,应当加强现有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综合实力、执法专业化水平和人员配备,协调好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关系,并适时将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相对独立的、专业化的权威执法机构,最终通过保障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主体的不断创新,为整个社会和消费者的福祉贡献力量。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312/04/456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