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也有望帮助相关电厂达到这个相对严格的环保要求。相比于亚临界燃煤机组,超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的燃煤温度更高(约760摄氏度),内部压力也更大(超过3万多千帕),因此发电效率也更高。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后文简称CAP)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能效最高的100家燃煤电厂中超过90%配备了超超临界技术设备,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仅为0.76%。显然,中国在这一方面步子迈得比美国更大。
为了巩固超临界机组升级带来的能效提高,北京还推出了其他一系列措施。比如在生产环节,企业开始广泛采用煤炭粉碎技术和大型流化床锅炉。此外,政府还鼓励投资煤热解、煤气化、碳捕集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简称CCS)等技术,积极推动煤化工产业发展。据了解,电力生产和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有近9成都可以通过CCS技术封存在枯竭的油气田和无法开采的煤层中。值得庆幸的是,相比于亚临界和超临界电厂,在超超临界机组中添加CCS技术设备相对难度反而更低。

中国煤电产业:内部差异不容小视
的确,中国在燃煤电厂绿色改造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但是要想成为全球清洁能源模范领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中国在能源开发和碳排放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别。真实情况总要比眼前所见要复杂得多,这也可以算作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目前,中国在政治、地缘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具备了推动国家能源政策向清洁化方向转型的条件。比如,中国政府之所以会推出“清洁煤炭”计划,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息中产阶级对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满。此外,通过前沿技术大幅度削减碳排放也可以彰显政府的减排意愿,有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积极落实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相协调”的施政方针。然而,中国政府这种自上而下分配排放份额和制订能效标准的做法本身也存在一些弊端,因为它给不同地区的不同电厂留下了不少违规的空间。
比如,安装超高能效低排放(high-efficiency low-emission,后文简称HELE)设备会导致电厂前期成本高出20%到30%。对于享受政府补贴的大型电厂来说,消化这部分成本并不困难,而小型电厂则负担不起了。因此,中国现有燃煤电厂中仍然有48%属于能效水平较低的亚临界电厂。除电厂之间的技术差别外,欠发达的煤炭产区(比如内蒙古和宁夏)与临海发达地区之间能效水平也有差别。巨大的地域差别也让中国政府试图在全世界面前展现的从上至下一致环保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对中央的环保目标和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需求,污染严重的地区常常会陷入两难境地。
清洁煤炭技术:方兴未艾?
尽管存在上述差距,但是中国仍然为全球树立了榜样,证明了可持续发展不一定就是可再生能源与煤炭之间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
和中国一样,印度也已经成功地走上了向清洁能源转型的探索之路。据统计,印度燃煤发电占全国发电总量的72%。印度政府在能源问题上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认为煤炭和清洁能源都是印度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印度政府目前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不仅要保证3亿无电人口用上电,同时还要达到《巴黎气候协定》的环保目标。为了完成这些目标,印度试图通过CCS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实现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比如,一家印度企业就通过碳捕集技术,用其燃煤锅炉排放的碳制作小苏打。此外,印度政府还将高能效低排放(high-efficiency low-emission,简称HELE)技术提上了日程。根据这一计划,2020年前印度将对4000万千瓦机组进行超临界技术升级,同时还将建设一座装机总量为80万千瓦的超超临界电厂。
如今,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也开始积极探索清洁煤炭技术。为了完成《巴黎气候协定》目标,全球第三大煤炭生产国澳大利亚计划将现有燃煤电厂升级为超超临界电厂,争取将碳排放总量降低28%。而全球第四大煤炭消费国日本也已经在矶子区火电厂(Isogo thermal power station)安装了两组能效为45%的高能效低排放(high-efficiency low-emission,简称HELE)燃煤机组。2011年大地震导致日本核电站受损严重,为了弥补由此带来的电力供应缺口,日本政府专门兴建了这座矶子区火电厂。
目前,中国还不足以成为全球环保领域的“尖子生”,而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则正在执行务实的能效政策,同时努力避免中国式自上而下模式的各种弊端。也许中国可以和它们一起来共同弥补美国留下的能源政策空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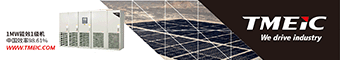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