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电集团副总经理谢长军建议,从立法角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跨区辅助服务机制,明确规定东、南部发达省份对西部富余可再生能源电网的接纳业务,并对受电方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从而打破地方政府条块分割的现状,下好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全国一盘棋。
此外,朱明认为,已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明确了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的有关要求,但今后工作重点要在明确责任,并通过能源监管的手段,强化落实、保障效果。
可再生能源补贴方式将调整
记者在上述研讨会上了解到,除了严重的弃电问题,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不足的问题也愈发突出。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处长支玉强直言,“截至今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缺口累计达到550亿元左右。尽管第六批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很快要下发实施,会缓解一定的压力,但是随着可再生能源新增规模的不断扩大,到年底预计突破600亿元还是很有可能的。”
据了解,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实行标杆电价,高出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部分,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而基金的主要来源是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截至目前其已经上调了5次,达到1.9分/千瓦时。
“理论上2016年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能达到800亿元,但实际征收的数额并没有这么多。”支玉强分析,“造成现在这种补贴资金缺口很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备电厂规模的快速扩大,由于它们基本不交或者较少地缴纳包括可再生能源附加在内的政府性基金,因此可再生能源附加的理论征收额度与实际征收额差别比较大。”他还表示,大幅度地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增加工商企业的电价负担,不符合宏观经济的形势需求,这也说明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难以为继。
在他看来,《可再生能源法》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应对拒绝缴纳可再生能源附加的行为有明确的追究处罚规定,同时补贴资金来源方面的法律规定存在歧义,第20条规定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来源于电价附加,但在第24条又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来源既包括国家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也包括电价附加,这样就造成了在实际执行中,有关部门莫衷一是。
谢长军也表示,可再生能源立法存在着一些问题,部分法律条款还不够完善,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未能有效指导地方政府科学合理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同时,立法缺乏环保条款。
支玉强透露,随着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和绿色电力证书的交易机制的建立,我国现行的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也将相应调整和完善。首先组成电价的两部分——燃煤标杆电价和财政补贴要分离,以适应当前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需要;把差价补贴模式变成定额补贴,并且逐步降低标准,同时补贴的方向也会调整,更多地倾向于分布式。此外,推进配额制和绿色证书交易机制,通过市场来发现补贴的标准,最终的目标是要取消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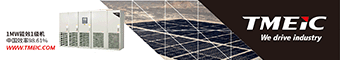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