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转型需要新措施
中国能源转型需要新措施,跨越实现能源结构的演进与转变。当前世界能源转型均处于初期阶段,但各国有所差异。总体上,欧盟一些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国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能源消费增速减缓,能源结构与能源效率不断改进,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单位GDP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持续下降。但从转型的基础来看,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与已完成两次能源转型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能源转型的任务非常艰巨。从经济发展水平对能源价格承受力来看,中国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能源转型必须要有更强的变革才能与其他国家同步进行。中国能源结构的演进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依次完成由煤炭到油气,再从油气到可再生能源的变化,而可能要直接进入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发展阶段,跨越式地演进和迭代式地发展。
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资源量是否充足,二是价格是否被市场所接受。总体来看,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可以满足能源转型的需要,但分布不均衡,2020年,一些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可率先实现平价上网。我国要实现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一是要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要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目前,尽管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能源利用效率改进幅度较大,但在资源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条件下,要在2050年完成转型,仍需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技术创新活动在经历短期低潮后开始恢复,技术创新渐趋活跃。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存贮和传输技术进步步伐加快,提升了新能源利用效率和发展速度,新能源产业发展日渐成熟,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不断下降,竞争能力日益增强。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中国在减排问题上,显示一个大国应尽的责任。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源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的生产与消费,解决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重要出路是改变能源结构,减少化石能源生产与消费,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建立更加高效、清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与此同时,要实现降低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要以大幅度提高能效为主,控制煤炭和能源消费总量。总之,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中国的减排任务非常艰巨。中国的国情也决定了中国能源转型需要采取新的行动。
从四个方面做好体制机制建设
促进能源转型,需要探讨能源产业政策。能源转型有多种路径和政策工具选择,选择的标准简而言之就是成本低、效果好。我国实施的能源产业政策主要包括能源补贴、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3类产业政策。由于我国能源消费基数大、速度快,为了实现减排承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亦是能源宏观管控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有必要结合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以及新问题,对我国已实施的能源产业政策进行评估调整,形成更好的政策组合。
政策实施的效率是以体制为基础,体制机制是能源转型的重要保障。从能源转型的客观需要出发,中国当前体制机制改革与建设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有利于能源转型的电力市场建设。新能源利用主要是以发电的形式,电力市场体制建设至关重要。在电力体制改革过程中,要注意以能源转型为重要目标,建立适应新能源发电的电力系统,发展智能电网和电动汽车,促进跨区域电力交易,开展新能源发电的辅助服务,在条件许可的地区,推动可再生电力与其他能源的综合供应。
二是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政策。虽然2020年以后,一些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能不再需要补贴,但是从总体来看,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相比在较长时间内仍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存在一定的缺口。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及其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要实现发挥导向作用,注意对分布式发电的补贴,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的利用率,优化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来源,保持补贴政策的稳定性。
三是要发挥产业对节能减排的积极作用。产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能源消耗的主体,另一方面也是推动节能减排和能源转型的技术载体。能源转型要坚持以产业为重点,强化节能减排措施,一方面降低能源需求增速,另一方面强化低碳清洁技术的供给与应用。要大力发展低碳绿色农业,积极构建低碳的工业体系,实施服务业的绿色发展,加强行业准入管理,规范新能源产业发展。
四是建立健全能源转型的投资机制。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需要巨大的投入。资金投入不足会严重影响能源转型。要强化新能源产业的投融资机制建设,完善金融服务,扩大银行业对新能源产业的信贷支持,鼓励金融创新,推进与新能源相关的金融产品开发。完善资本市场,实现新能源产业金融支持的多元化,加快设立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促进新能源投资主体多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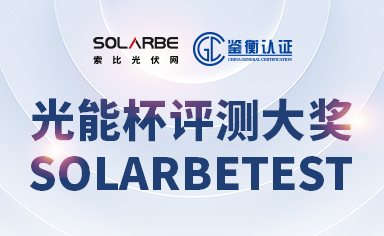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