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兰一家的生计都在鹅背上。她穿着一双黑色的粗跟皮凉鞋,上面有好几块已经干了的泥渍,也有新沾上去的。她抬脚给人看,“一出去一脚泥巴,好看吗!”她也想早日搬走,但新家没钱装修,只有靠种地、养鹅、摸鱼慢慢攒钱。
因为沉降,从前的厨房门框像被压弯了的扁担,现在用来当鹅圈。以前水还没来的时候,他在家里感到“下面放炮开采,房子在动。”
她丈夫也在矿上干过一两年,怕得职业病就离开了。“讲得挺恐怖,石头能把人压成饼。”
出去打工也没有门路,“早前做临时工,经常遇到不给钱的。给就给,不给就去磨。要不到就算你倒霉。”
朱正兰的家凌乱得让人很难还原出它以前的样子,家具都展现着灾难过后七零八落的模样:无处不在的裂缝,大衣柜拦腰截出被水泡过的痕迹,破了洞不再修复的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淹,修它干啥。”
一面墙上有她女儿6岁时画的画,如今女儿已结婚。另一面墙上有他丈夫写下的“恒心”和“海纳百川”。
如今是“水纳我家”。每一年夏季,朱正兰都要搬走一次。“水上来了,我们就往上面跑呀。”她家的小电视不大,“搬起来就走”。
一下雨就害怕,一夜醒来,锅和鞋子都漂起来了,他赶紧把家当装上三轮车和拖拉机,撤退。
水下去得慢,要个把月时间。朱正兰坐在一袋尿素上发愁,“屋里很少干,水离我们越来越近,离房子越来越近。”
30年前嫁到这个村子里,朱正兰对它谈不上喜欢,“人可能因为穷,就特别自私。有的人把田埂往别家移,占这种便宜。”但这里曾经有垂柳下的小河,有她喜欢的肠道相连的宅子,有长满草的土丘和铁路线。种着果树的村子一直往前延伸,通向各家田地。若干年前村子的居民曾为获得多一寸土地而争吵过,如今那些生产粮食的沃土只能长出水下植物。
“大势所趋,”农妇朱正兰说,“你不能改变事实。”在这一季的汛期来临时,她必须尽快离开。
三
在谢家集区的老鳖塘,蔡瑞豹一家的日子是在岛上过的——如果能称之为岛的话。
老鳖塘是早年挖煤产生的塌陷湖,中间延伸出一条狭长的陆地,这块土地上总共住了4个人,两位看门的大爷和蔡瑞豹两口子。
蔡瑞豹是鱼贩,有这个职业常见的凶气。人如其名,他说父亲曾希望他霸气一些,现如今,“还‘豹’呢,给水里淹着了。”他站在水塘中间说。
他往前后一指,“这边是李一矿,这边是谢二矿,这边是李二矿。”这些矿早已停产,留下老鳖塘。
蔡瑞豹家世代在此生活,“小时候想去矿上挖煤,但年龄不够人家不要,好不容易年龄够了,矿上工作要走关系,农民没钱,又没土地,只能养鱼。”
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打鱼,然后运到集市上卖。渔网散落在房间周围,水涨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就划船进出,水走路。第一次家被水淹时,这个壮汉说,心里难受,皱着眉“想哭”。
家里的冰箱给垫高了,墙上爬着青苔,蚊子苍蝇多。如果刮风,晚上睡觉他能听见水声。他和老婆要喝水,得拿桶到镇上装,每次够喝上三四天。
老鳖塘周围还有些村庄,水悬在它们头上,一些房屋已经画上了拆迁的符号。一位老人戴着矿工帽在门前溜达,他1996年退休,有38年的工龄。他刚工作时李一矿投产没两年,火车站只有两个铁皮筐子。
他指着坡上的树说,“以前,地跟那树一样高。”
在他看不到的很多国家,煤矿勘探者必须提交详细的土地复垦方案才能开工挖煤,并对之后的生态恢复提供资金。
老井是矿上的工人,缺乏社交才能,但会写诗。他和他的诗出现在纪录片里、文学刊物上,他穿着下井的矿装,与各种名人合影,身上的反光条强烈地反着闪光灯的光。
“地球上两百年前没有煤矿工人,两百年后可能也不会有,我们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有责任把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
他写过一首《塌陷湖》:一颗硕大得足以填平苦海的清澈泪珠/默默地荡涤着天地间的尘埃与荒凉/多少苦难与悲怆/都圣贤般地在这水底沉淀……
“看到塌陷湖,我的内心很矛盾。”老井戴一副金属框眼镜,“虽然我不是产煤能手,也不是领导,但我是矿工之一,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始终有种愧疚的感觉。”
他把塌陷湖称为“大地表面的伤口,积满雨水”,是“矿山心间的一滴泪”。
在这座城市疯狂产煤的时期,大车拉着优质煤、煤矸石以及煤泥来来回回,煤泥黑乎乎、稀稀的,一边拉一边往下滴,给这里的道路留下黑色遗迹。
“遗迹”随处可见。在淮南,没什么高的建筑物,因为地下是空的。出租车司机陈明开玩笑说,淮南建地铁都不用打洞了,直接铺铁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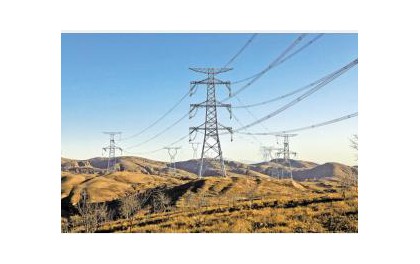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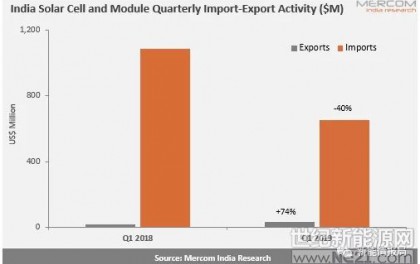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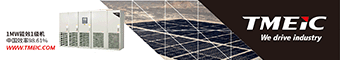











 >
> >
>
